周晓虹:变迁时代的观察者
- 2017-03-08 11:39:00
- admin 转贴

群学书院创始人周晓虹
01
2015年南京大学高研院十周年庆典时,举办了一个“学术伉俪”系列讲座活动。周晓虹和夫人朱虹是其中一对嘉宾。周晓虹是社会学教授,朱虹是管理学教授。报告厅挤满了听众。
周晓虹和朱虹的学术领域有一些交集。比如,消费主义。周晓虹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《文化反哺: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》,就谈到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与消费革命的兴起。这本书,从萌发灵感到完成,整整用了25年的时间。
周晓虹调侃,如果让讲究效率的商学院教授来写的话,可能只要两个半月,但他认为很值。“从1988年到今天,这么长的时间、这么多的变动,才使议题的讨论有了更宽广的论域。用25年邂逅一个宏大的场面,非常有意义。”
文化反哺,是周晓虹1988年提出的概念,用来指在急速变迁的时代,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。这个词近年逐渐从学术界走向大众,已经成为一个流行概念。2010年,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就是从角色转换谈文化反哺。

02
1985年,周晓虹的父亲从部队离休,领了一笔服装费。父亲给了他200元,让拿去买衣服,但规定不能买西装。在父亲脑子里,西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。周晓虹当时还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,他背后虽然已经穿上了牛仔裤,但这200元钱却严格接受了“投资人”的决定。
但三年后,1988年的大年初一,父亲拿出一套西装,让周晓虹教他打领带。“当时我就震惊了。父亲也穿西装?从来严肃的父亲,竟然也为此向我请教。”周晓虹立即嗅到一些变化,这成为文化反哺概念的最初由来。这一年,周晓虹写了《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》一文,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。
1998年,周晓虹正在专心研究苏南和温州农村的比较,写出了博士论文《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》。
这年里的一天,他听到好友美学教授周宪跟人谈电脑,谈不过了,使出杀手锏:“不对,不对,我儿子说……”。周晓虹像触电一样,立即问旁人,听到没,他在说什么?大家并不以为然。
就是这句话再度给了周晓虹“社会学想象力”。他意识到,文化和知识的来源,判断对错的标准,开始从老一代到了年轻一代手上。“《文化反哺》这本书的副标题,‘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’,为什么是革命?因为两代人的关系整个颠倒过来了。”
学富五车的美学教授的论证方式,证明了新的文化传承方式的出现,甚至预示了一种全新社会的到来。在数字化时代,亲代甘愿拜子代为师的现象,是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亲子关系“颠覆”的特例。

03
周晓虹开始做一些案例研究。最先在南京选择了7户家庭,在北京“浙江村”选择了2户家庭,做田野调查和焦点组访谈。此时,人们对“文化反哺”的概念,还持“谨慎肯定”的态度。但调查结果出乎预料,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,父母向孩子学习已经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,“高知”父母也不例外。研究结果让周晓虹相信:文化反哺这个概念是成立的。
此后十多年,周晓虹继续做这项研究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和重庆五个城市做了77户家庭的访谈。从食品、器物、行为方式、价值观等各方面,对文化反哺现象作了全方位的解读与分析。
在他看来,计算机是父母人生的“滑铁卢”,原来“无所不能”的父母开始在计算机面前败下阵来。手机,也体现了代际沟通的主导权,从上一代转移到下一代。访谈写道:几乎所有父母都承认,在操作手机上,尤其是发短信方面自己极其低能,这构成了他们向子女学习的内容之一。
文化反哺是当今中国独有的吗?
周晓虹认为,中国的特殊性在于,作为一个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,经历了30年的封闭、停滞后,突然剧烈转型,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“至尊”到“落伍”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。因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两代人的差异之大是绝无仅有的。
《文化反哺》写到三分之二,周晓虹被查出患了“肾癌”。他做好了一切准备,结果手术前一天检查,核磁共振却发现没有问题。经历了一次“生死”,他在书的后记里写了一段很煽情的话:“爸爸,我终于写完了。我用我的心血将我们父子因心灵的碰撞激起的一束情感的浪花,开掘成了一条汪洋恣意的大河!”

04
1990年代初,周晓虹注意到,在中国市场上,羞答答地出现了第一本以中产阶层趣味为定位的《时尚》杂志,其基本主题是倡导中产阶层“消费、消费、再消费。”而当时,在大多数人脑中,过度或超前消费仍是一种“错误”的观念。
2001年,“想象力”丰富的周晓虹开始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。他是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之一。2005年,他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和武汉五个城市做调查,为当时的中产阶级画了一副像:月收入5000元,有大专以上学历,主要从事脑力劳动。他认为,在这五个城市,有12%的人达到这个标准,“现在觉得这个数字保守了。”
这一调查发布出来,引起一片质疑。几周后,在Google搜索“周晓虹+中产阶级”,有75400条消息。上海的一位白领把每一笔收支晒到网上:月入7000元,除掉开销,每月只剩下200元。他质问周晓虹,我也算中产阶级吗!?而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,年收入6至50万,也引起了争议。
“当时人们确实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层。”周晓虹感到很疑惑,“改革开放快30年了,为什么很多人对中国存在中产阶层持怀疑态度。”

05
2005年秋天,周晓虹去印度开会,在德里的一个三星级饭店,跟大堂经理闲聊,问他是不是中产阶级。大堂经理的月收入相当于人民币1000多元,但却自信地说,of course,I am middle class。接下来,经理的下一句话,差点让周晓虹惊掉下巴:“你不知道吗,我们印度是中产国家”。那一刻,他想起了100年前访问芝加哥的韦伯,而孟买正像当时的芝加哥。
就是在这一年,印度号称有7亿中产阶级。为什么两国对中产阶级的认识有那么大偏差?周晓虹想了很久,发现,中国人对中产阶级的否认,可能源于对“middle class”这一词的误读。
“中国人一向很注意这个‘产’,强化了人们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,而忽视了现代中产阶级或者说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。其实中产阶级,就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,如果不受雇于人,除了自谋生计的个体户,那可能就是资产阶级了。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,官方多用“中等收入阶层”一词来替代。”
另外,周晓虹认为,人们对中产阶级和中产社会产生了混淆。一些学者写文章反驳,以中产社会的五条标准作为理由:第一,城市化率达到70%;第二,白领工作者大于或等于蓝领工作者;第三,恩格尔系数降到0.3以下;第四,基尼系数保持在0.25至0.30之间;第五,人均受教育12年以上。显然,对照以上几条,中国远远不够。
“我显然不认为中国已进入了’中产社会’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,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,‘金字塔型’不复存在,但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、底部更大的‘洋葱头’,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还面临许多严峻的考验。”
周晓虹认为,中国中产阶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尽管它像股市和楼市一样,多少有些泡沫。但他的态度十分鲜明:一方面,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刚刚开始,具有相当的上升空间。另一方面,从不幻想中产阶层的成长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。

06
周晓虹曾下乡插队两年。在农村时,他很喜欢写东西,小说、诗歌都写,创作热情很高,在田间地头宣传队要上台,他五分钟就能写出一首诗来。1977年,恢复高考,670万人参加考试,录取27.8万人。周晓虹考取了南京医学院医学系。他没有考中文系,“那时候傻乎乎的,觉得文学家都从医生出来的,郭沫若、鲁迅,所以就想干脆学医吧,就这么简单。”
进了医学院,他还是“不务正业”,继续写小说,鼓捣伤痕文学。年纪稍大,理性渐长,发现当年写的小说,就像调查报告,已不能卒读。于是放下小说,研究起社会学。“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,一切百废待举,再说我一看那时领头的又是费孝通先生,我就考到南开去,把自己的一生都改过去了。”
1990年代,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野蛮的活力,高校教师纷纷下海。1993年周晓虹碰巧到海南授课。先期下海的南开和南大两所学校的十位朋友来接他,十辆豪华轿车一字排开,让他随便挑,想上哪辆上哪辆。周晓虹上了一辆最豪华的车。半路上,十数位武警端着冲锋枪跳出来,喝到:把手举起来。朋友说别怕,估计是“出事了”,例行检查。第二天报纸报道,海口一家银行被抢走50万元,打死两人。
下了车,一行十几人向烧烤城走去。领头的朋友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,像黑社会老大,两排女服务员齐刷刷地鞠躬,大喊“请”。朋友说,看到了吗?这就是金钱的力量。周晓虹现在还能记得朋友当时的表情。
那时,他的月薪是一个月150元,三个人住学校的宿舍里。朋友们的月薪都是5000元以上,还有原始股。朋友说,干脆甭回去了。周晓虹还是回去了。1992年,周晓虹给仪征化纤写了一句广告语:“仪征化纤,与世界共经纬”,得到一万元报酬。后来那句广告语出现在各地的机场码头。当老师能维持兴趣,还能挣点外快,过得比较宽裕。朋友的飞黄腾达,没有给他太多刺激。
“如果换种生活方式能让挣的钱以几何级数增长,我也许会放弃兴趣;但如果只能以算数级数增长,当然兴趣第一。”周晓虹说,“其实商人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,我跟他们一样,只是角色不同,Calling(天职)不同。我在课堂上的满足感也很强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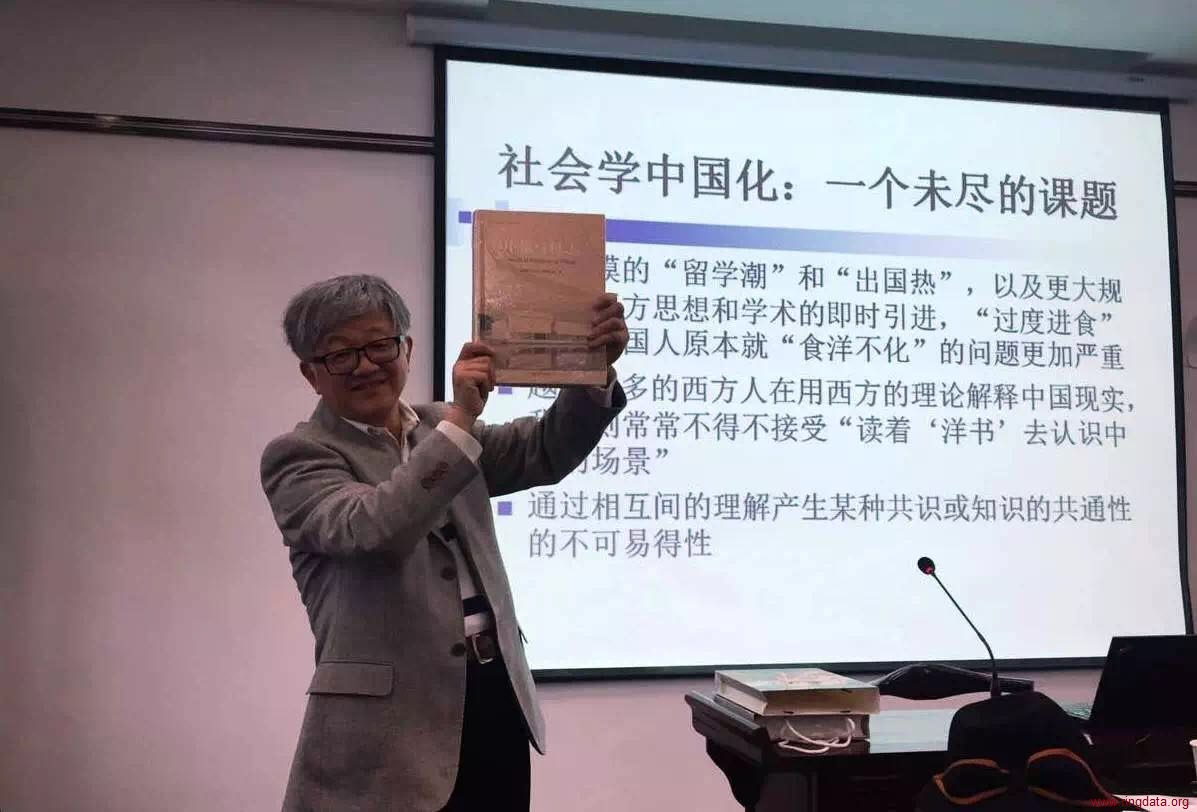
07
在南大的一次学术午餐会上,新闻系教授潘知常笑言:周晓虹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遗憾。
在周晓虹看来,遗憾其实是有的。“当你用25年完成一本书,而你又有许多研究兴趣时,你会感到以生之有涯对知之无涯,非常悲凉;我一生想写很多书,而留给你的时间只够写两三本好书,怎么会没有遗憾?

